Review and Prospect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ath for “Non-grain” Cultivated Land
-
摘要: 梳理“非粮化”管控措施,探讨未来“非粮化”管控的重点方向,可以为“非粮化”管控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基于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总结“非粮化”的概念、类型、现状、原因、影响以及治理措施。结果表明:当前对“非粮化”的概念与类型尚未达成一致,我国“非粮化”现象呈扩大趋势且经济发达地区与南方地区“非粮化”率较大,“非粮化”原因主要包括种粮经济效益低、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耕地资源多宜性、政策执行偏差、农户自身因素;不同的耕地“非粮化”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存在较明显差异。针对“非粮化”问题所采取或建议的措施,包括法规措施、经济措施、破坏鉴定措施、规划措施,但是目前关于利用差别管控措施治理“非粮化”的研究数量与深度尚且不足。针对当前管控存在的法理说服力较弱与治理隐患性较大的问题,建议今后在耕地保护法律中设立相应条款,并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在县级划定粮用单元、食用单元、农用单元,制定各管控单元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与差别管控办法。Abstract: Summarizing the “non-grain” control measures and discussing the key direction of “non-grain” control in the futur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on-grain”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uctive reaso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types, current situation, causes, impact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non-gra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urrent researche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non-grain”. The phenomenon of “non-grain” was expanding in China and the rate of “non-grain” was higher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and southern regions. The causes of “non-grain” mainly include low economic efficiency of grain cultivation,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multi-suitability of arable land resources, deviation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other factors related to farmer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non-grain” on the quality of arable land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measures taken and suggested for the problem of “non-grain” included regulatory measures, economic measures, damage identification measures, and planning measures. At present, the amount and depth of research on making different control measures for cultivated lands are insufficien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weak legal persuasion and great hidden dangers i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suggestions on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should been in the farmland protection Laws in the future, and the grain units, edible units and agricultural units should be demarcated at county level according to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scope of production, operation activities, and differential control methods of each control unit should be formulated.
-
Keywords:
- Cultivated land /
- Non-grain /
- Big food view /
- Land use regulation
-
国际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再次让人们意识到了粮食安全、食物保障对于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性。我国自古重视“耕读传家”,农耕文化传承不息,同时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问题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用土地流转带动规模化经营[1-2],但在流转展开的同时也伴随出现了一些“非粮化”现象。近年来,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加剧趋势威胁着我国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状况,影响耕地在“餐桌”与“田间”上发挥应有功能。202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做出了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的决策部署。鉴于“非粮化”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亟待解决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本研究对“非粮化”相关问题与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立足大食物观,探讨规划措施,提出管控路径与思路的展望。
1. 耕地“非粮化”概况
1.1 耕地“非粮化”概念
关于“非粮化”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定论。刘洋等[3-4]界定“非粮化”概念为:出于对比较效益的追求,原本用于传统粮食作物生产的耕地,转向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高效农业,用于良种繁育等其他非粮食作物生产用途。关于“非粮化”的内涵,吴郁玲[5]总结相关学者的研究,概括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上的耕地“非粮化”是指在耕地上种植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行为;而广义上的耕地“非粮化”则是指在耕地上从事一切“非粮化”种植的行为。本研究综合上述学者观点,从土地利用角度,暂拟耕地“非粮化”的概念为:经营主体违反相关规定,擅自将原本种植传统粮食作物的耕地用于其它农林牧副渔业的经营活动。
1.2 耕地“非粮化”类型
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类型。朱道林[6]从实践角度,将“非粮化”分为三类,一是耕地撂荒;二是利用耕地种植经济作物甚至改为鱼塘、养殖池等;三是利用耕地种树。李超[7-8]从产出产品的主要用途角度,将“非粮化”分为种植非粮食类食物、非食用农产品、非农产品三大类。郝士横等[9]从利用的主要形式角度,将“非粮化”分为发展林果业、挖塘养殖、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发展设施农业、开展乡村旅游。亦有地方政府组织文件中界定了“非粮化”类型,如信阳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1年10月28日成文、11月8日发布的《全市流转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专项整治方案》中对于流转耕地“非粮化”的整治类型包括:流转永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以及挖塘养鱼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流转的永久基本农田闲置、荒芜1年以上的行为;流转永久基本农田发展稻渔、稻虾、稻蟹等综合立体种养,沟坑占比不符合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通则标准的行为。工商资本、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流转耕地违规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的行为。工商资本违反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非粮化”行为。
1.3 耕地“非粮化”现状
1.3.1 全国现状
2021年8月26日,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从“三调”数据看,2019年末全国耕地为19.18亿亩。“二调”以来的10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1.13亿亩,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亿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可见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任其“肆意发展”将威胁耕地红线。
1.3.2 区域现状
孔祥斌[10]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统计数据,初步判断目前我国耕地“非粮化”率约为27%,但是全国各地区耕地“非粮化”的类型、程度存在差异。第一种是食物性生产的“非粮化”,华东地区“非粮化”率约为21%;华南地区约为41%;华北地区约为10%;华中地区约为34%;西南地区约为46%;西北地区约为32%;东北地区约为7%;黄土高原地区比例为30%左右。第二种是非食物性生产的“非粮化”,如:北方种植杨树、景观林、草坪;南方种植桉树以及一些区域景观化建设。可见从区域差异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南方地区的“非粮化”率较大。
1.3.3 近十年研究文章状况
以知网中“篇名”搜索2012年至今的“非粮化”文章为例,共搜集到264篇文章。从研究趋势来看,如图1(a),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21年达到峰值,应与政策的发文时间与社会关注度有关。主要研究机构方面,主要包括四种,一是政府机构、二是农林类高校、三是综合类高校、四是财经类高校。词频统计情况见图1(b),排名前十位的热词依次为粮食(10102个)、耕地(9145个)、农业(5493个)、生产(5416个)、土地(5011个)、流转(4745个)、种植(4567个)、农户(2704个)、面积(2618个)、发展(2394个)。
1.4 耕地“非粮化”原因
1.4.1 经济效益低
谷贱伤农是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对于“非粮化”而言,种粮经济效益较低是其重要原因。一方面,种粮成本、土地流转成本越来越高,而粮食收购价格相对较低;另一方面,“非粮化”利用带来的经济高于种植粮食作物,面对种植粮食作物比较效益低下情况,农户除了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外,亦可进城务工以增加收入[3-16]。
1.4.2 地区发展水平差异
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而言,对经济作物、特色农产品有着较多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周边农户的“非粮化”生产供给。此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大家从“吃饱”转变为“吃好”,从而有了更多样的饮食需求,甚至居民对休闲观光旅游的追求也有所提升,亦促进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增长。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使得劳动力流失,相比发达地区有着更多撂荒耕地的现象[6,11,17]。
1.4.3 耕地资源多宜性
毋容置疑,耕地自身的质量限制性因素、本底条件、适宜性等自然条件影响着经营主体的利用方式、种植选择、使用强度,同样影响着“非粮化”的类型选择。孔祥斌[10]指出优质耕地资源本底条件的多宜性强,既可以种植粮食作物,又可以种植经济作物,是耕地“非粮化”的资源基础。陈美球等[18]指出对于耕地土壤的养分平衡与恢复,合理安排耕作制度、适宜进行作物轮作,益于维持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
1.4.4 政策执行偏差
易小燕[19]认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龙头企业带动流转、大户规模化集中流转、专业合作社集体是三种引起“非粮化”的主要土地流转模式。关于农业补贴的有效性与激励性,靳庭良[20]认为补贴的类型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王为萍和赵姚阳[21]认为补贴政策未能使真正种粮者受益。此外,一些地方把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理解为压减粮食生产,为带动经济选择性忽视耕地“非粮化”问题,以及部分地区不合理的乡村振兴措施,亦成为耕地“非粮化”的诱因[22-26]。
1.4.5 农户自身因素
农户是耕地利用中的行为主体,其种植行为选择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户在劳动力转移、性别结构、年龄、历史情结等自身因素的异质性均会影响到种植方式的选择。以及在粮食安全危机意识方面,相关农户只看到了耕地“非粮化”后短期的利益,对潜在危害认识不足;以及农户之间看到“非粮化”利用带来的利益后进行模仿、跟风,形成了一种趋势[5,9]。此外,农户种植技术、投入成本、设施条件等经济物质条件影响着耕作的难易程度与种植方式选择,同样会对耕地“非粮化”产生影响。
1.5 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1.5.1 耕地本身质量
“非粮化”有很多利用类型,虽然每一种利用类型都可以被称为“非粮化”,但不同的“非粮化”现象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别,并不是所有“非粮化”利用类型都会使耕地土层中相对优质的耕作层受到破坏。例如种植经济作物、合理的水旱轮作、用养结合等行为基本不会破坏耕作层。一些“非粮化”利用类型会对耕作层造成一般破坏,例如在设施大棚内的地面铺设砂石、砖块后种植食用菌,种植绿化花卉苗木(售卖时会带走部分耕作层表土)等。还有一些“非粮化”利用类型会对耕作层造成严重破坏,例如种植速生杨、速生桉等根系发达的树种;挖塘养鱼、挖湖造景会导致耕作层直接丧失且逆转难度大;设施农业中建设建筑物、硬化地面等行为同样会使耕作层受到破坏[7-9]。也有学者研究了“非粮化”的生态效应,杨朝磊[27]以云南为研究区,得出耕地过度“非粮化”对土壤环境、水生态环境与大气环境均会产生严重影响。
1.5.2 参与主体
对参与主体而言,张华泉等[28]通过博弈模型,指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下,中央政府的目标出发点在于增加全社会福利水平;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是追求经济增长、提升地方官员政绩,农户的出发点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主体间存在博弈。因此,非粮化带来的收益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方与农户的短期发展需求,从而引起更多的“非粮化”现象,但长远来看不利于维护中央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2. 耕地“非粮化”治理措施
对于如何妥善治理耕地“非粮化”现象,政府部门与相关学者从法规、经济、破坏鉴定、规划等路径入手,采取措施或给出相应建议。从这几方面治理路径的逻辑来看,法规措施的治理逻辑在于“制度”,以制度为基础,便于管控的法理依据与解释;经济措施的治理逻辑在于“奖惩”,通过“奖”来提高农户、地方的种粮积极性,通过“惩”去处罚一些“非粮化”利用产生的破坏耕作层等影响耕地生产能力的行为;耕作层破坏鉴定措施的治理逻辑在于“衡量”,衡量“非粮化”行为对耕地种植条件的影响;规划措施的治理逻辑在于“管制”,运用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手段,达成治理目的。
2.1 法规政策措施
2.1.1 国家层面——防止“非粮化”
针对耕地“非粮化”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下半年相继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和《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长牙齿”的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2021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亦将耕地保护作为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这一部分提出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
2.1.2 部委层面——“进出平衡”
2021年11月26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2021年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重点问题整治的通知》。2021年11月27日,《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均提出“进出平衡”,细化“非粮化”治理措施。
2.1.3 地方层面——“田长制”
为加强耕地保护力度,北京、山东、安徽、黑龙江等地结合当地情况,均探索推行出台了关于推行“田长制”的相关文件,提出建立起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主要目的,以责任制为核心,以地方实际为定位的网格化管理的耕地保护机制[29]。
2.2 经济措施
2.2.1 经济机制
对粮食主产区而言,一方面肩负较多粮食产量,另一方面也面临种粮效益低、耕保成本高的矛盾,使得地区的经济收入受到影响,使不同功能区间的粮食生产责任分配不公的问题加剧。对耕地本身而言,也存在着高质量地块(基本农田)收益较低的矛盾。有学者建议规划管制措施要符合经济规律,将粮食补贴政策、农业综合开发政策、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等,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挂钩,设立永久基本农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的经济机制;同时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在基于规划管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耕地的流转费指导标准,引导土地流转费处于合理水平[6]。也有学者建议构建统一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提供粮食安全公共物品,实现粮食安全的公平提供和对农民利益的保护[30]。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按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要求,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2.2.2 耕地价值损失估价
有研究以估价方法对耕地破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价,包括造成耕地本身价值损失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耕地修复所需成本的间接经济损失[31]。也有学者研究了关于耕地“非农化”过程中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估算,也可以为针对一些“非粮化”行为所造成的耕地价值损失评估提供借鉴思路[32]。
2.3 耕作层破坏鉴定措施
郝士横等[9]依据目前我国尚未设立“非粮化”耕作层破坏认定国家标准现状,结合耕地“非粮化”现象,通过土地评价的方法拟定了包括耕作层厚度、人为侵入体含量、砾石含量、土壤环境质量、pH、有机质含量、容重、耕层质地、生物多样性、盐渍化程度十项指标的耕地“非粮化”耕作层破坏诊断标准,进行耕作层破坏鉴定,评价破坏程度。李超[7-8]选取耕作层厚度、土体构型、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污染、土壤容重、杂物侵入(有害杂草、固体侵入物)、生物多样性等八项指标。
2.4 规划分区管控措施
苏越[13]以桐乡市为研究区,结合耕地多功能评价,拟定三级五区的耕地“非粮化”分区管控措施:第一级为粮食生产核心区,禁止一切“非粮化”生产,限期恢复已开展“非粮化”生产的地块;第二级包括生态农业区、复合农业区和休闲农业区,其中生态农业区内允许适度发展花卉苗木种植等环境污染小、生态可持续性高的“非粮化”类型;复合农业区允许粮食生产结合某些“非粮化”养殖生产,发展复合农业生产;休闲农业区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允许适度发展休闲农业项目。第三级为一般农田区,可在不破坏耕作层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非粮化”生产。卢艳霞[33]认为当前亟待研究制定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化管制规则,在全国总量上平衡好“粮与非粮”,在区域尺度上保护好资源禀赋特点和特色优势农业品种。
3. “非粮化”管控路径展望
面对耕地“非粮化”倾向,如果任其发展,将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采取合理的举措管控耕地“非粮化”现象,可以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有必要以当前“非粮化”治理存在的不足为导向,提出相应的管控路径展望。
3.1 “非粮化”管控困境
3.1.1 法理说服力较弱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有自主组织经营和处置产品的权利,亦规定应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当前“非粮化”治理是为了将耕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这样地方行动时就存在一定的“法理漏洞”与“法理偏差”:工作中向经营主体说明要停种经济作物、改种粮食时单单以政策变化为由,明显法律依据和说服力度不够强。
3.1.2 治理隐患性较大
面对公民膳食多样化的需求增加与农户增收的需要,要多去“换位思考”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发生,如果“一刀切”似的全部禁止,或治理时不管不顾当前作物的生长状况,不顾忌现实情况与农户想法,可能造成“社会稳定”与“政府名誉”出现隐患。
3.2 设立《耕地保护法》
有学者总结立法途径和规划途径是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进行农地保护的主要措施[34-35]。针对“非粮化”的一些具体行为,我国已有相关法律对其进行了明确禁止,如《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但目前我国尚未针对耕地设立专门的《耕地保护法》,对于粮食安全的支撑与农耕文化的载体而言,为弥足珍贵的耕地资源设立一部《耕地保护法》既满足管理需求,也可以成为夯实耕地保护制度的硬措施[29,36]。
所设立的《耕地保护法》(或其它名称的耕地保护相关法律)针对耕地“非粮化”现象设立的条规,一是剔除法理模糊,明晰上述与《农村土地承包法》之间的模糊之处,明确经营主体对耕地利用的权利界限。二是明确粮食概念,面对当今居民膳食结构的变化与“大食物观”,耕地粮用其中这个“粮”的概念,是否需要延伸,纳入油料、果蔬等。三是保护耕地生产能力,立法保护耕地,除了面积红线,重点要保护耕地的种植条件与产粮能力,要限定对耕地的利用是可持续利用,不可破坏耕作层、不可减少有效土层厚度、不可损耗种植条件等。四是要有奖惩措施,在地方有效完成耕地保有量等耕地保护任务时给予奖励,进一步保障农户种粮收益,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同时,对于破坏耕作层、种植条件等不当利用行为,予以处罚。五是将田长制、责任制纳入此法,加强耕地种植情况的巡查与监管。
3.3 依据空间规划,形成管控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基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主要手段[37]。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到2025年时,要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在空间规划中划分单元,是国内外的通行做法。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单元,是县以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空间变化监测的区域,也是一个规范化、信息化和法治化的规划平台。规划单元以县(市、区)域为整体,每个单元系统是相对独立的功能板块[38]。耕地保护与耕地“非粮化”问题当然可以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相应的规划单元,将二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以贯之的管控体系,为粮食安全、藏粮于地提供依据与支撑。
管控体系的形成与搭建,一是注重地域差别,要以县级为基础与纽带,根据不同地区的“非粮化”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二是注重掌握现实情况,根据耕地自然以及立地条件,结合自然界限、人工界限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去做以规划,用能用、管用、好用的规划去治理“非粮化”存量、遏制“非粮化”增量。三是注重差别管控,合理划分粮用单元、食用单元、农用单元,并进一步细化不同单元的耕地用途管制,严格规范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如允许、限制、禁止),制定破坏耕作层、影响耕地自身种植条件的负面清单。同时,面对不同“非粮化”类型与作物的不同生长情况,不能盲目“一刀切”,不要全部是刚性管控、也要有弹性措施。四是注重人本思想,结合本地区人口情况、综合粮食需求情况、耕地保有量、生活空间需要情况,去合理布局、划定单元。除上述粮用单元、食用单元、农用单元外,也可结合地方实际,划一些特色单元,如田园综合体单元、特色农产品单元、农业公园单元等,打造“农田生态 + ”、“田园生活 + ”的效果。
3.4 立足大食物观,实施差别管控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日趋多元化、品质化与营养化,在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可以立足大食物观,构建“食物安全”的概念与战略[39]。
“非粮化”管控单元的划定方法,可以在整合各类空间规划基础上,因地制宜,分析当地耕地“非粮化”的空间格局、驱动机制,运用形态特征、监测、调查、3S技术、田长巡查等识别方法判定出耕地“非粮化”的具体田块[40-44],评价这些田块的耕地破坏程度。合理划定不同情境下的管控单元土地用途区域,明确耕地用途管制的内容、管制规则及利用负面清单。通过在全国范围以县级为基础的定边界、定用途、上图库,划定不同情境下耕地用途区域,明确不同情境的管控规则,制定每个类别的管制措施与处置办法。
具体“非粮化”管控单元举例如下(图2),粮用单元:核心要义围绕“粮食安全”,突出耕地生产功能,充分发挥粮食供给能力,确保区域谷物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此单元实施刚性管控措施,禁止一切“非粮化”生产。食用单元:核心要义围绕“食物安全”,面向农户增收与人民膳食结构多元化需求,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耕地多宜性,兼顾农民增收,“粮果蔬菌副”高收益发展。此单元针对那些不会破坏耕作层、“非粮化”后种植食用农产品的利用行为,允许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生产等相适宜、相结合。农用单元:核心要义围绕“乡村振兴”,面向农业经济收益提升与城乡休闲体验需求,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关联区域农业、经济、社会、生态正向协同发展,丰富区域内乡村的社会活动空间、激发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美丽乡村建设、提高农业生态环境。此单元针对那些不会破坏耕作层、“非粮化”后种植与经营非食用农产品、项目的利用行为,允许结合实际,适度发展花卉养殖、花海观光、农田观光等休闲农业、生态农业项目。这样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人民膳食结构,并增加农民利益收入,提高地方农业经济收益,带动主产区抓粮积极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研究方面,当前“非粮化”的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但针对“非粮化”实施差别管控、分类施策的研究数量与深度尚且不够。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化管制规则亟待研究与解决。
(2)治理方面,当前“非粮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法理说服力较弱以及治理隐患性较大。面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仅以政策变动为由去管控“非粮化”,明显法律支撑力度较弱。此外如果面对复杂的“非粮化”现象采取“一刀切”的管理办法,存在一定治理隐患。
4.2 建议
结合对当前“非粮化”管控措施的梳理与分析,建议今后在以下三个方面对“非粮化”现象进行管控与治理。
(1)总体管控思路方面,建议从农户角度(增收)和公众需求角度(膳食结构变化)角度出发,以利农惠农为根本、以大食物观为方向、以耕保立法为基础、以规划体系为依据、以差别管控为举措。
(2)法律法规方面,建议针对耕地“非粮化”现象在《耕地保护法》中设立相应条款,主要围绕法理模糊的剔除、耕地利用权力界限的明确、粮食概念的界定、耕地生产能力的着重保护、奖惩措施的设立、责任制的构建。
(3)差别管控方面,建议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以县级为基础划定管控单元,围绕“粮食安全”、“食物安全”、“乡村振兴”分别划分粮用单元、食用单元、农用单元,并规范各单元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与“非粮化”行为管制措施。
-
-
[1] Su Y, Li C L, Wang K, et al. Quantifying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multi-aspect performance of non-grain production during 2000–2015 at a fine scale[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9, 101: 410 − 419. doi: 10.1016/j.ecolind.2019.01.026
[2] Liu Y, Yan B J, Wang Y, et al. Will land transfer always increas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hina? —A land cost perspective[J]. Land Use Policy, 2019, 82: 414 − 421. doi: 10.1016/j.landusepol.2018.12.002
[3] 刘 洋. 流转农地中的“两非”问题研究[D]. 湖南: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4] 匡远配, 刘 洋. 农地流转过程中的“非农化”、“非粮化”辨析[J]. 农村经济, 2018, (4): 1 − 6. [5] 吴郁玲, 张 佩, 于亿亿, 等.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与展望[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9): 116 − 124. doi: 10.11994/zgtdkx.20210909.102404 [6] 朱道林. 耕地“非粮化”的经济机制与治理路径[J]. 中国土地, 2021, (7): 9 − 11. doi: 10.13816/j.cnki.ISSN1002-9729.2021.07.03 [7] 李 超, 王 巍, 李伟成. “非粮化”利用对耕地质量的影响[J]. 中国土地, 2021, (3): 17 − 19. doi: 10.13816/j.cnki.ISSN1002-9729.2021.03.06 [8] 李 超, 程 锋. “非粮化”对耕作层破坏的认定问题思考[J]. 中国土地, 2021, (7): 12 − 14. [9] 郝士横, 吴克宁, 董秀茹, 等. 耕地“非粮化”耕作层破坏诊断标准探讨[J]. 土壤通报, 2021, 52(5): 1028 − 1033. doi: 10.19336/j.cnki.trtb.2021010801 [10] 孔祥斌. 耕地“非粮化”问题、成因及对策[J]. 中国土地, 2020, (11): 17 − 19. [11] 张藕香, 姜长云. 不同类型农户转入农地的“非粮化”差异分析[J]. 财贸研究, 2016, 27(4): 24 − 31. [12] 周 霞. 耕地与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对策[J]. 山西农经, 2021, (14): 48 − 49. [13] 苏 越. 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与管控研究[D]. 浙江: 浙江大学, 2020. [14] 宋卫庆, 岳建伟. 耕地“非粮化”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以山东省阳谷县为例[J]. 宁夏农林科技, 2020, 61(1): 26 − 29. doi: 10.3969/j.issn.1002-204x.2020.01.009 [15] 张宇鑫. 我国耕地非粮化问题研究述评[J]. 农业与技术, 2021, 41(19): 21 − 23. doi: 10.19754/j.nyyjs.20211015006 [16] 赵和楠, 蒋炳蔚, 赵炜涛. 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21): 81 − 84. doi: 10.13546/j.cnki.tjyjc.2021.21.016 [17] Zhao X F, Zheng Y Q, Huang X J, et al.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Farmland Transfer on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Non-Grain Farmland in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17, 9(8): 1 − 19.
[18] 陈美球. 耕地“非粮化”现象剖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土地, 2021, (4): 9 − 10. doi: 10.13816/j.cnki.ISSN1002-9729.2021.04.03 [19] 易小燕, 陈印军, 王 勇, 等. 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J]. 农村工作通讯, 2011, (15): 21 − 23. [20] 靳庭良. 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3, (17): 91 − 95. doi: 10.13546/j.cnki.tjyjc.2013.17.034 [21] 王为萍, 赵姚阳. 流转农地“非粮化”利用研究[J]. 陕西农业科学, 2015, 61(8): 98 − 101. doi: 10.3969/j.issn.0488-5368.2015.08.031 [22] 刘 航, 张莉琴. 农地流转会导致农地利用“非粮化”吗?−基于地块层面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 2020, (11): 45 − 53. [23] 常 伟, 马诗雨. 农地规模流转中的“非粮化”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 2020, (9): 3 − 5. doi: 10.3969/j.issn.1001-6139.2020.09.001 [24] 周艺霖, 宋易倩. 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形成原因与化解对策−基于国家粮食安全视角[J]. 广东农业科学, 2016, 43(1): 189 − 192. doi: 10.3969/j.issn.1004-874X.2016.01.033 [25] 王 勇, 陈印军, 易小燕, 等. 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问题与对策建议[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1, 32(4): 13 − 16. [26] 薛选登, 张一方, 李 珂, 等. 河南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及对策探究[J]. 南方农业, 2017, 11(5): 66 − 68. [27] 杨朝磊, 李灿锋, 田瑜峰, 等. 云南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及其生态环境效应[J]. 矿产勘查, 2020, 11(12): 2573 − 2591. doi: 10.3969/j.issn.1674-7801.2020.12.001 [28] 张华泉, 王 淳.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流转用途规制可有效抑制“非粮化”倾向吗?−基于三方动态博弈的视角[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7(3): 59 − 65. [29] 吴克宁, 郝士横, 吕欣彤. “田长制”相关问题分析[J]. 中国土地, 2021, (12): 10 − 11. [30] 徐浩庆, 李维峰. 粮食安全、土地用途管制和农民利益保护分析−基于二元经济和公共物品提供的双重视角[J]. 经济问题, 2021, (11): 88 − 97. doi: 10.16011/j.cnki.jjwt.2021.11.011 [31] 潘元庆, 谷志云, 王 涛. 耕地破坏鉴定机构现状分析及建设构想[J]. 中国土地, 2019, (4): 31 − 33. doi: 10.13816/j.cnki.ISSN1002-9729.2019.04.10 [32] 杨文杰, 刘 丹, 巩前文. 2001—2016年耕地非农化过程中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估算及其省域差异[J]. 经济地理, 2019, 39(3): 201 − 209. [33] 卢艳霞, 王柏源. 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的演进及其逻辑[J]. 中国土地, 2022, (2): 4 − 8. doi: 10.13816/j.cnki.ISSN1002-9729.2022.02.02 [34] 赵学涛. 发达国家农地保护的经验和启示[J]. 国土资源情报, 2004, (6): 43 − 47. [35] 钱素梅. 美日两国耕地保护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 西部资源, 2013, (5): 185 − 186. [36] 孟敬雯. 耕地保护的法律制度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11): 31 − 33. doi: 10.3969/j.issn.1007-7103.2021.11.012 [37] 林 坚.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M]. 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21. [38] 吴次芳. 国土空间规划[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21. [39] 吴克宁, 郝士横. 耕地保护献策[J].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 2022, (1): 10. [40] 陈 浮, 刘俊娜, 常媛媛, 等. 中国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分异及驱动机制[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9): 33 − 43. [41] 何飞霏, 邓乐莹, 许怡欣, 等. 基于卫星遥感影像的南方村落耕地“非粮化”信息提取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15): 11 − 14. doi: 10.3969/j.issn.1007-7103.2021.15.005 [42] Su Y, Qian K, Lin L, et al. Identify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non-grain production expansion in rural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licies o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J]. Land Use Policy, 2020, 92: 104435. doi: 10.1016/j.landusepol.2019.104435
[43] 关小克, 王秀丽, 赵玉领. 黄河沿岸“非粮化”耕地形态特征识别与优化调控研究[J]. 农业机械学报, 2021, 52(10): 233 − 242. doi: 10.6041/j.issn.1000-1298.2021.10.024 [44] 常媛媛, 刘俊娜, 张 琦, 等. 粮食主产区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分异及其成因[J].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1, (7): 1 − 11. doi: 10.13254/j.jare.2021.0337 -
期刊类型引用(19)
1. 张擂,周煜明,董杰谋,李祥,刘时栋,徐丽萍. 中国耕地非农化与非粮化时空分异及其治理策略. 干旱区研究. 2025(02): 372-383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2. 刘序,梁俊芬,凡超,冯珊珊. 基于高分二号的都市农业区域土地覆被时空变化研究. 四川农业科技. 2025(03): 5-9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3. 丁学谦,汪立,易家林,金军伟,谭永忠. “良田”变“粮田”:组织场域视角下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宁波北仑区的案例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25(03): 80-9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4. 刘旭峰,陈文明,杨益民,肖云,罗灵岭,张福林,朱山昱. 基于GWR模型的湖南省耕地非粮化驱动因子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25(02): 93-10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5. 曹振. 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法治进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2): 43-53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6. 罗浩轩,郭栋.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2): 11-2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7. 秦涛,邵战林. 新疆新型城镇化与耕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安徽农业科学. 2024(07): 259-263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8. 陈磊,王诚成. 四川省安宁河流域耕地非粮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土壤通报. 2024(02): 331-340 .  本站查看
本站查看
9. 陈莉珍,刘光盛,聂嘉琦,肖瑶,杨丽英,王红梅. 耕地“非粮化”影响因素空间效应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4(03): 530-53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0. 牛金枫,马艳杰,晋鹏飞,张美萍,陕永杰. 粮食产销平衡区耕地非粮化时空分异及驱动类型.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4(04): 769-779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1. 董雨瑞. 耕地“非粮化”法律规制的局限与完善对策. 中南农业科技. 2024(08): 188-193+199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2. 吴小晶. 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法律规制.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4(22): 188-19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3. 关小克,王建骁. 基于系统思维的耕地高质量治理路径研究.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6): 53-60+71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4. 曹琳琳,杨子生,杨人懿. “非粮化”、“大食物观”与粮食资源配置.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4(12): 1783-179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5. 廖磊,于志磊,蔡利平,吕宜平,刘立杰. “耕地大占补”改革背景下耕地保护智慧监管系统设计与实现——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 山东国土资源. 2024(12): 49-55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6. 张育超,刘健,姚志. 农业强国视域下中国耕地“非粮化”的动因与治理综述. 安徽农业科学. 2024(24): 10-16+2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7. 黄建伟,岳明翔. “非粮化”与“趋粮化”:央地政策冲突、基层行为策略及其治理. 土地经济研究. 2024(02): 1-17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8. 白洋,董雨瑞,李姿莹. 耕地碳汇与粮食安全保障协同推进的制度完善. 世界农业. 2023(08): 76-87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19. 梁坤宇,金晓斌,王世磊,应苏辰,祁曌,周寅康. 综合“同质等效—流补平衡”的耕地“进出平衡”管制:方法与实证. 中国土地科学. 2023(07): 77-8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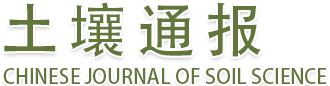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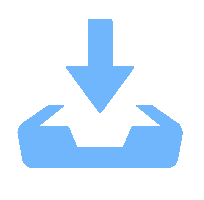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